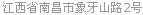|
北大荒的女人垦荒老兵的妻子们大多有腰腿疼的毛病,这是常年劳作而且是在恶劣的环境下透支体力做下的病。她们追随丈夫来到北大荒,她们嫁到了北大荒就从没有想过离开,她们的男人在这儿,她们的家就在这里。垦荒官兵们在北大荒吃过的苦,这些女人一样没少吃,甚至,比男人更苦更难。男人忙于外面的工作,根本顾不了家。在他们的心中,工作永远比家务事重要,而那个为他们生儿育女、给了他们温馨和安定的女人,似乎永远都在默默地理解他们,因为她们明事理,宽容,吃苦耐劳。她们不会埋怨、不会叫苦,更不会影响他们的工作。所以,有的时候他们肆无忌惮地消耗着这一份纯厚、亲情和爱。“她生这个孩子的时候,接生婆说,快回家看看吧,你老婆马上就生了。我正在猪号,母猪也要下崽了。我和接生婆说,我没有时间,你看着吧。那天七个母猪下崽子,每个都下十来个小崽子。我那时候是畜牧副队长,虽然有饲养员、班长、排长,但是很晚了,不想让不值班的人都来,他们明天还要工作。再说这样的事做得多了,也不是什么难事了。”当年的赵凤宣这样做的时候,一点儿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甚至没觉着是什么难事,他是料定了妻子不会跟他闹跟他翻脸,甚至都不会给他个脸色。不过,如今的赵凤宣说这番话时,还是有着内疚的:“我顾公家顾大家,顾不了小家。她带着两个孩子,挺辛苦的。”正在哺乳期的女职工也享受不到特殊关照,仍然要参加劳动。有的地号离住地十多里地,中间休息,要跑回家给孩子喂奶,喂完奶再跑回地里干活。持家相夫、养儿育女,这是女人的天职;而这些家属们参加工作,往往干的又是最底层的劳作,工资却是最低的,不过这也使这些女人欣喜不已。农工的身份,让她们被社会认同,也有了除贤妻良母之外的价值。殊不知,她们的付出与被认可的价值是不等同的,她们得到的工作,带有赐予的意味,随时都有可能被剥夺被削弱,还不能有微词,还得欣然接受。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即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农场削减开支,精简裁员,首当其冲的,就是把参加工作的家属们都劝退回了家。说服动员工作由她们的男人来做,干部、党员带头;甚至不用这样麻烦,一声令下,不管有多少不解委屈不甘,女人们都得乖乖地回到家里,成为名副其实的家庭妇女,还得照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因为她们是家属,男人的附属。张宪文的老伴张秀英说:“他不当指导员嘛,我不下会有人攀的,我就得带头下。退职还让我们干临时工,还得干活,不干不卖给你粮。就是说,农场是缺劳动力的。他从来不管家,他一来当副连长,天不亮就要去割草、挑草去,家根本就管不了。当指导员更忙了,都得跑地号,就我自己管家呗,管家还得上班,四个孩子都养大了。”勤劳朴实、纯厚善良、贤妻良母,都可以用在她们身上。她们是最传统的中国妇女,没有非分之想,不贪图荣华富贵,丈夫是她们的天,嫁了,就随了,同甘共苦,荣辱与共。她们没有多少文化,但她们有最纯朴的道德基因;她们没见过什么世面,但却有着最宽厚的心胸;她们也没有多么高的觉悟,但却懂得不贪便宜、不靠丈夫的地位获利、不给自家男人惹麻烦,甚至,替丈夫分担一份责任,或者,干出自己的一番事业来。北大荒的女人,跟她们的男人一道,创造了另一番垦荒风景。1.侯桂花:拿着60块钱从山东老家找到八五二农场付孟海的妻子侯桂花当年是拿着60块钱找到八五二农场的。她从山东老家坐车到长春,又从长春到密山,从密山到宝清。到宝清遇到一辆汽车,问人家,你知道有八五二吗?人家说知道,却不肯带她去。她就在那里转悠,趁着司机下车去办事,偷偷爬上了车。“到了种畜站,南面有一间草房子,她向人打听:你这是不是五队呀?人家就和她开玩笑,说不是五队是六队。她干脆坐那儿不走了。”付孟海至今认为他媳妇挺能的。她比他大一岁,来北大荒的时候她二十五岁,他们的女儿七八岁。她没有多少文化,却比他能,脑子好用,人缘好,会说话会办事。“哪像我,当个窝囊干部,就知道干活。”付孟海当时在劳改队当管教,领着劳改犯伐木、割草、盖马架子、修桥、修路。侯桂花参加工作后,当过菜组班长、妇女委员。她把这份工作做得风生水起的。她能给死人穿衣服。老人有讲究,要穿着新衣服走,人没气再穿新衣服就不好了,她会掌握时间,知道那人什么时候断气。这是死人的事。“活人呢,两口子干架,她给人劝架,别离婚,别干架。她三句话就把那小伙子说得没话。她能抓住理,她真能把死人说活了。她尽干这事。”“我说不过她。人家说我,你不行,你尽瞎说,你看你老伴说话,尽是道道。”“我当副连长,涨工资没有我的事,连队涨工资可困难了。党小组三十多个党员,一致同意给她涨工资。有人提意见,老付啊,你老伴提工资了,怪好的。连长说,别怨老付,是全体党员一致同意的,她干活好,团结同志好,人缘好。”付孟海从心里佩服他的老伴。“我属鸡她属猴,谁说鸡猴不到头?我们都八十多岁了。”2.张秀冶:第一个孩子就是干活累掉的,抬大麻袋呀孙锡恩的妻子张秀冶是领着两个弟弟背着行李跟随丈夫来的。她是奔着享福来的,说是这里有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还有大米饭吃。可是一下车,却发现,这里连个正儿八经的房子都没有,一个马架子住两家,哪有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呀?孙锡恩夫妇更可气的是,小咬蚊子扑面而来,挥之不去,气得她自己打自己的脸,禁不住感叹:这是什么地方啊?但是,张秀冶没想着离开。她的两个哥哥都是当兵的,她的家也是革命家庭,她不能给他们丢人。她嫁给他了就跟着他,再苦再累也要在这待着、咬着牙挺着。张秀冶在老家时是人民代表,还是妇女队长,到了农场就是普通农工,工资25块钱。丈夫在队里当个干部,却从来不照顾她,她干什么也不管,能干就行。张秀冶身体好,肯干,哪有需要出力的活就找着她,种地,抬麻袋,做豆腐推磨,刨厕所的粪,甚至挖坟坑、埋死尸。那时候的家属们都这样,所有的杂活都归了她们,但大地里的活也不少做。她们单独成立了一个班,叫十二班,割大豆时那些男农工都干不过她们。“一听见喊十二班加油,我们这些老娘儿们虎了吧唧的,就使劲干。”“那时候就知道干活,不问有多钱。在农场还挣过工分呢,我是最高的,以我为标准。涨工资我是最多的。”“我第一个孩子就是干活累掉的,抬大麻袋呀。”孙锡恩却顾不上她,他正领着人开荒,给开荒的人送饭;他还开拖拉机、扶犁,检查开荒质量。什么时候天黑了才知道回家,可回来吃口饭就又去办公室了。家里的活丈夫一点儿也帮不上,割草、打柴火都是张秀冶自己干。孩子小的时候,要出去时,她就把孩子绑在炕上。“那时候的日子不能提了。”“你看见了吧,我现在腰也弯了,腿也瘸了,也遭罪呀,都在地里干活。现在享福了,我也有病了,瘸啦瘸啦地走不了了。腿疼,膝盖疼。”3.刘凤琴:男人在外面开荒种地,家里全靠我一个人管赵景财的妻子刘凤琴是被公公护送到北大荒的。那时候,她和赵景财结婚刚一年多。他们虽是一个村的,但刘凤琴家是后搬来的,赵景财当兵出去了,所以他们不认识。他从部队回家探亲时,经别人介绍,他们见面了。“他大我十岁,他那时穿便衣显得年轻。他愿意打篮球。我们认识不到一年,年,我就到部队和他结婚了。年一月份他送我回老家,四月份他就来北大荒了。”赵景财夫妇先来一年的赵景财经常去虎林接人,接来自各地的复转官兵,然后安排他们转去八五二农场。那天,没想到,他接到的是自己的父亲和妻子,还有九个月大的儿子。惊讶过后,赵景财把他们送到了迎春,自己返回去继续接人。从迎春下车以后就没有车了,刘凤琴背着行李,老公公背着孩子,一路走到了八五二农场。到处都是烂泥,没有路,刘凤琴去食堂吃饭,小心翼翼地走,还是摔了一跤。洗脸时要拿脸盆到外面?点雪,化成水再用。先是住马架子,后来的住处也是临时的,四家一个屋,对面炕,一个炕住两家,炕像土堆似的,是凉的,还不能烧火。有一次还安排住进来一个大姑娘,用箱子隔着,就等于一个屋住了五家。“后来又住旅店,一头住旅客,我带孩子住一边,老公公挨着旅客住。没住多久,又搬到一个人家住,一个炕,又住了好几家。就这样住到十月份,招待所的房子盖好了,分了一间,好歹是一家一个屋,别提有多高兴了。”那房子在当时可是最好的,瓦房,筒子楼,没有自来水,得下楼去挑水。赵景财天天在外面忙,这楼上楼下挑水、扛柴火的事都是刘凤琴自己干。年,总场组织机关家属成立了大集体被服组,洗衣服、做衣服,有个小木板房当车间。刘凤琴兴奋不已,孩子小还得抱着呢,那也要上班。丈夫把自己的表卖了,换了一台缝纫机,她就开始给人做衣服。年时,这些家属填了张表,才算正式上班了。年轻时的赵景财赵景财一天到晚地在外面忙工作,家里的事根本顾不上。刘凤琴一个人撑持着这个家。生老二时,还在月子里,下雪天,她抱着大儿子去粮店买粮。生老三那天早上,赵景财说要上分场去,刘凤琴告诉他肚子疼,赵景财让她等着,他下午回来,然后就走了。刘凤琴一看,这又指望不上了。两个孩子一个六岁,一个四岁,还什么都不懂呢。她把两个孩子的衣服都洗了,到自家地里摘回一个面瓜,煮了吃点,医院就吃不上饭了;还去排队买了一块肉回来,也煮熟了。眼看着天黑了,赵景财还没回来,她就给孩子弄点吃的,医院用的被子包好。“我要走时,他回来了,问我,你干啥去?我说玩去。我都要哭了,不知道他想没想着我,他就光想着工作了。”当天晚上刘凤琴生下了老三,医院陪着她。农场的男人都忙,农场的男人都不知道照顾女人,家属们只得自己找帮手。“我们三个女的一起怀孕,男人都不照顾,都是互相照顾,到医院陪着。”“生完了,就请人用担架把我抬回来了,家里还有两孩子呢。我在家待了两天,自己洗衣服洗尿布。他就知道上班。”“我这一生啊,真是不容易。男人在外面开荒种地,家里全靠我一个人管,也不觉得累。我可愿意干活了。”4.孙淑梅:我也挺傻的,那么小就嫁给他,到北大荒来遭罪了王龙祥的妻子孙淑梅是辽宁丹东人。抗美援朝时,王龙祥没有过江,在丹东空二军招待所办公,负责给去朝鲜的军人“签证盖章”,他们戏称是“过江护照”,就是办理通行证。部队驻防四道沟时,孙淑梅小学6年级毕业,8月份他们就结婚了。孙淑梅18岁,小他10岁,什么也不懂,连婚姻都是继母给包办的。王龙祥夫妇年王龙祥转业时有二个去向,一个是回原籍浙江金华,一个是去北大荒。孙淑梅不愿意去南方,俩人就选择到北大荒来了,也是奔着“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来的。到了密山,赶上下雨,脚被烂泥黏住,拔不动腿,家属们感觉受骗了,都是二十几岁的年纪,就抱在一起哭。哭完了,也没别的选择,还得跟着男人走。从宝清坐上了大板车,走了一天,晚上到了四分场四队。住的是劳改犯住过的房子,在屋子里拢了一堆火,没有灯,也没有蜡烛。大家睡在一个屋里,一家挨着一家,对面大炕,一步就能迈到对面炕上去。炕都塌了,也不能烧火,不知道劳改犯是怎么住的。房子有门框没有门,有窗户没有玻璃,四处透风,睡觉都得戴着狗皮帽子。就这样住了半年。孙淑梅没想长期待在这里。那时候全国各地都来农场调人,最近的是调去齐齐哈尔富拉尔基。念到谁家男人的名字,谁家的女人就高兴。孙淑梅很期盼能听到自己丈夫的名字,但每次都念不到他的名字。他老实,干活踏实,农场愿意留这样的人。由于人员外流的厉害,年以后就不往外调人了。孙淑梅也就断了走的念头。家属们算农工,一个月挣二十五元,和男人们一起出工。男人到草地割草,女人往外背草,在草筏子上,动不动就陷进去了;男人刨坑,女人点籽,孙淑梅还感觉挺好玩的。第一次割大豆,孙淑梅穿了一双挺漂亮的水靴,第一刀没有割掉大豆,把水靴割了个大口子,她心疼死了。王龙祥一直当干部,在工作上对自己的妻子却一点也不关照。“我一直在外面干活,有两个锄草的人就有我一个,有割地的人也有我。冬天刨粪,上猪号、牛圈、马号去积粪,往地里送粪。我没有怨言,什么活都得有人干。“下班回来就要做饭吃,还要忙活孩子,吃完饭就要开会,你不去开会今天的工不给你记。就得把孩子锁在家里。他有事没事晚上都去办公室,天天如此,年年如此。“人是有福能享,有罪能遭。大家都那样生活,你不也得那样生活嘛,一挺就挺过来了。我的思想挺单纯,没有想这想那的,怎么能把家里的日子过好,怎么把他照顾好,把孩子管好就可以了。“我没有什么文化,我也挺傻的,那么小就嫁给他,到北大荒来遭罪了,呵呵。”5.谢新兰:把孩子扔在家里就上车了,农场培养你就得干活孙略的妻子谢新兰是北大荒第一代女拖拉机手。第一代女拖拉机手谢新兰他和她是同乡,两家隔十里地,是别人介绍认识的。年的时候,他们在部队结婚,孩子刚满月,他就接到紧急任务,这个任务还不许带家属,他便把她和孩子送回了老家。返回部队不久,部队大裁员,他转业了。他和湖南省军区的复转官兵一起,坐上湖南省军区的一趟专列,那是一辆闷罐车。闷罐车直达密山,然后这支部队一起被分到了八五二农场。那是年的三月份。年三月份,谢新兰在老家收到一封信,信里有一张照片,孙略站在东方红54上面,很是威风。她看过报纸上登载的中国第一代女拖拉机手的事迹。此前,她只是羡慕,没觉得跟自己有关,她都没摸过拖拉机。此时,看到丈夫站在拖拉机上的照片,她忽然意识到,这事儿跟她有关系了。谢新兰来到八五二农场二分场五队,投奔她的丈夫。丈夫没在家,上山伐木去了。她看到的家,就是马架子。尽管有许多的不适应,但她留下了,丈夫在这儿,她就不能走。她成了一名普通的农工。五队是刚建的点,丈夫在机务,天天开着拖拉机开荒,农工排上山割草、伐木,盖房子,搭马架子。总场招考拖拉机手,谢新兰闻讯很兴奋,毫不犹豫就报了名,她正怀着身孕,此时刚两个月。她是高小文化,考一般理论对她来说不难,她考上了,是八一农大附属中专,在四分场。年11月份到总场报到,学习一年。说是学一年,其实是边学边干,掌握了基本要领,就上车了。八五二农场一共有七八个女拖拉机手,她们成立了一个包车组,叫三八包车组。女拖拉机手跟男的一样干活,开荒,种地,也打夜班。“六零年五月三十号播种,我站在播种机上,一下子滑到地上。我都怀孕八个多月了。”幸好,孩子没事,谢新兰挺着肚子还接着干。6月21日,谢新兰生了,是个儿子。11月份,全分场统一秋翻地,拖拉机是主力。“我把孩子扔在家里了,给他喂点东西就上车了。就得去啊,农场培养你就得干活。”谢新兰后来调到分场修配所工作,是个技术工人,五级钳工。孙略说:“她在机务上是一把好手,在家里是贤内助。”谢新兰说:“我开拖拉机没开够。”6.贡彩南:嫁给了垦荒军人,与北大荒结了一辈子的缘采访贡彩南是在苏州,这是她丈夫叶亦祖的老家,她的老家是江苏丹阳。叶亦祖在十多年前过世,她与女儿女婿在一起生活。她性格很开朗,爱笑,还健谈,头脑十分清楚。她说的是普通话,带着江南口音,却很好分辨,这是北大荒生活留下的痕迹。年轻时的贡彩南已经八十岁的老人仍然精神头十足,腿脚利落。平日里做饭、上街买菜、去医院看病、参加老友聚会,甚至去美国探亲,都是自己去。老人说,我不想给女儿添麻烦,只要能走能动,自己的事情就自己做。每天早上起来给孩子们做做饭,也是一种动力,心里有事,就不犯懒,还能锻炼身体。“前两年还每天坐公交车去游泳馆游泳呢!”她曾担心在北大荒艰苦的生活和劳动条件会让她做下关节病,幸好,腿没落下什么大毛病,或许是因为她只在北大荒待了八年,比那些在北大荒待了一辈子的女人要幸运;但不期然就发作的哮喘病,还有腰肌劳损,却是北大荒的极寒天气和强度劳动留给她的病根,每每让她痛苦不堪。但是,问她是否后悔去了北大荒,老人毫不犹豫地说,“不后悔,一点儿也不后悔。”就这八年的时间,已是她一生的财富。老人说,“如果没有那八年,我不会有现在这么好的生活;没有那八年的锻炼,离开北大荒后的事业就不会干得那么有成就。”贡彩南退休时是苏州市汽车配件厂党委书记,还曾经当选苏州市沧浪区三八红旗手。至今,贡彩南还与北大荒有着多方联系,那些曾经的同事、邻居、同学,分散在天南海北,每每有人来苏州,她都热情接待。平日里通通电话,说说往事,互相安慰。她说北大荒的人好,当年在北大荒时结下的情谊,很特殊。离开北大荒多年后的第一次同学聚会是在无锡,来自全国各地、包括北大荒来的,大家见了面,都抱头哭。“都是在最艰苦的时候走过来的,感情不一样。”贡彩南在北大荒的时间,从年至年,正是北大荒最艰苦最难过的八年。年,贡彩南十九岁,刚刚中学毕业。贡彩南是从一位堂叔口中知道北大荒的。堂叔是铁道兵,年去了北大荒,这次回丹阳探亲,说起北大荒。堂说也只是说说,但贡彩南有心了。贡彩南自小父母双亡,寄居在叔叔家。叔叔家还有奶奶,有婶婶。奶奶和叔叔对她很好,可婶婶的白眼让她饱尝了寄人篱下的滋味。从四五岁开始,她就给人家放牛,稍大点就挑水、割草、割麦子。她很能干,也希望用自己的劳动换来住在这个家里的资格,但却事与愿违,每天端起饭碗,仍然得听着婶婶的唠叨,话里话外都是嫌她白吃饭,她溜边坐着,心里充满了忐忑。她爱读书,喜欢上学,但婶婶说女孩子书读多了没用,只让她读业余学校,后来是业余学校的老师见她爱学习成绩好,亲自去家访说服了婶婶,她才得以进入正规学校。待她渐渐长大,婶婶就开始托人说媒,总想把她推出去。堂叔口中的北大荒让她心动,不仅是能摆脱寄人篱下的生活,更让她神往。就这样,带着简单的行囊,贡彩南跟着堂叔走了,奔向了未知的北大荒。北大荒的天气真冷,她只带了一件小棉袄,穿在身上感觉如同纸片,让她饱尝了极地之寒。那雪下得真大,一夜狂风暴雪,门和窗便被封住了。因为刮的是西北风,住最西头的那家门前雪稍薄,人从里面用力还能推开,他出来了,便去挖隔壁邻居家的门前雪,把邻居放出来,然后,两人再一起去帮着挖第三家、第四家。每一次暴雪,都是这样,从西边开始,一家一家地挖,才能让住这一趟房的人们走出家门。原以为来了就能安排工作,不料却要等待半年之久,贡彩南不想吃闲饭,急着要找事情做。有老乡给介绍了一个差事,去四分场的场长家看孩子。这是保姆干的活儿,说好只是短期的,贡彩南同意了。场长是南通人,江苏老乡,家里有一个小孩。贡彩南是个闲不住的人,除了看孩子,还帮着烧饭洗衣。她干得太多了,以致主人家竟离不开她,说啥也不肯放她走,攀老乡的关系,还托人说情,说家里很需要她,说场长工作很忙,把场长家里照顾好了也是革命工作,硬是把她留住了。转眼又到了冬天。在贡彩南的坚持下,场长终于放她走了。贡彩南一早上就离开了场长家,步行回五分场找堂叔。出门时天气还是晴的,虽然冷,可有太阳照着,加之心情好,走起路来都是兴冲冲的。路况不太好,路面铺着冰,两边堆着高高的积雪,有一段还有“劳改”在修路。贡彩南急着赶路,几十里呢,得在天黑前赶到。不料,走到一半时,起风了,下雪了,风夹着雪吹在人脸上,像刀割,眼睛也被霜雪冻住睁不开,眯着眼睛看,四周白茫茫一片。身上御寒的衣物都是虚设,寒风从四面八方往里吹,像刺进了骨头里。她遭遇了人们常说的“大烟炮儿”!路上的积雪越来越厚,每走一步都很艰难,不知道前面还有多远的路;天黑了下来,旷野里没有人迹,还担心遇到野兽;她又累又饿,机械地向前挪着腿,心里不住想,这回肯定要死了……幸好,她遇到了两个人,也是赶路的,在这茫茫黑夜里,彼此都感觉亲得不得了。大家一起做伴壮胆,走在路上,也踏实了许多。天亮了,贡彩南终于回到了堂叔家。几十里路,走了一天一夜,她的两条腿都肿了。堂叔很是后怕,去找场长,请求给贡彩南安排个工作。堂叔说我把她带出来的,真出了事可担不起责任。场长答应了。贡彩南参加工作了,在五分场三队当农工,工资二十四元。她每月都往老家寄十块回家,奶奶老了,婶婶有风湿病,她能挣钱了,得报答她们。遗憾是,半年后奶奶就去世了。她知道了信,可她没有钱回家,就自己闷在屋里,痛哭了一场。春天了,开始播种了。刚垦出的黑土地,拿根棍捅一个眼儿,点上一粒豆种,用脚培上土,踩实了……十八岁的贡彩南憧憬起秋天的景象,想象着那一片丰收在望的田野,抑制不住地就想笑,“开心,天天开心得不得了!”几个月后,贡彩南被选送去农业技校。一辆马车将她送到了老场部,学校设在那里。她开始学的是农业机械,后来改为蓄牧兽医。不久,学校更名为八一农垦大学,招了许多部队的转业官兵。后来,学校又从上海招来一批学生,大城市的人,娇生惯养出来的,岁数还小,啥也不会干,连袜子都不会洗。贡彩南这一批老同学就承担起了照顾新生的责任,帮着烧炕、洗衣服,还要帮着砍柴。年冬天,最冷的时节,零下四十度,全校出动,到大孤山修水库,仍然是老同学照顾新同学。住的是马架子,几面就苫了一层草,透风露雪,晚上睡觉根本不脱衣服,还得戴着狗皮帽子。住处离工地很远,每天早上去晚上回来。白天的劳动强度很大,干得汗流浃背,棉帽上眼睫毛上都结上了霜;风很硬,一停下来浑身就冰凉的。晚上回来,棉胶鞋被雪水和汗水浸湿了,冻住了,要别人帮着才能脱下来。上海学生先睡下了,贡彩南等几个老同学还要帮他们烤鞋,一晚上都烤不干,自己的鞋都来不及烤。没有水,一个多月的时间,不洗脸不涮牙也不洗手,每个人的脸上都是黑黑的一层;喝的是雪水,把雪化了烧开了喝;吃玉米粒,也不洗,放进大锅里煮,一粒一粒的,很难消化。生活委员半夜发病,医院送,半路上就死了,胃穿孔。领导不让声张,保密,怕影响大家情绪,只几个党员知道,直到从水库撤回来才开了追悼会。他叫李佳期(音),四川人,从部队来的,刚24岁。“三年困难时期”贡彩南得了浮肿病。粮食不够吃,每天吃不饱饭,饿得走不动路,从宿舍到教室都得一步一步挪。学校食堂把柞树叶子和苞米芯加工了给大家充饥,一天三顿,吃得人都拉不出屎来。有的同学饿急了,跑到地里拣玉米,回来烘一烘就吃,还受了严重警告处分,开大会宣布的。冬天了,就吃冻罗卜,也没有油水,吃了一个冬天。麦收时,午饭才每个人发一个馒头,“吃得那个香啊,甜甜的。”从学校出来后,贡彩南做过八五二农场八分场的户籍员,管着一大片的户籍。要一家一家地调查、登记、填表、建户,确认哪些是农民、哪些是正式职工。农场的复转官兵好管理,身份都比较清楚,谁从老家带来的人,户口就落在谁家;但像杨大房这样的村屯就复杂,有职工还有农民,农民不归农场管,以前就放任了,现在得管起来,要掌握动态,上级要求时刻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她还做过粮食加工厂的统计员,当过出纳、卫生员,还养过猪。贡彩南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是在家里,遇到难产,丈夫急得束手无措,邻居们帮着叫来一辆“热特”,医院送。正是冬天,外面风吹得呜呜响,她能想像出坐着这“热特”行驶在坑坑洼洼的路上是个什么滋味。她坚决不去,说要死也死在家里。她让丈夫给她的一个同学打电话。同学在五分场,赶了几十里路到了八分场,帮她接了生。这同学是浙江人,八一农大时一个班的,学的也是蓄牧兽医专业。贡彩南说,“什么苦都吃过了,后来干什么事都没怕过。”因为去了北大荒,贡彩南的初恋无疾而终。还是在老家的时候,有一位男生对她很好,少男少女情窦初开,感情也是朦朦胧胧的。后来,男生去北京读建筑学院,贡彩南去了北大荒,两人一直都保持着通信联系,虽然没有明确表示什么,却也心照不宣。六零年贡彩南回老家探亲,特意去了一趟北京。两人见了面,说起北大荒,男生说他去北大荒肯定受不了,父母也不会同意。贡彩南听出这话的意思了,一个人回了北大荒,也把这一段感情沉进了记忆的深处。后来就遇到了叶亦祖,他上下铺的同学介绍的,也在八一农大读书,比她大八岁;转业前是空军领航员,在塔台指挥飞机,中尉。平时话不多,记性好,知识面很广,遇到知音打开话匣子就收不住。叶亦祖对她真好,知道她甲状腺肿大,就给她弄海带吃;他性子慢,脾气好,什么都听她的;他还特别能干,也从不拖她的后腿。叶亦祖离开学校后,当过八分场一队副队长,在蓄牧站干过,还当过分场副场长。年国家从农场调一批干部到南方,叶亦祖被选中。就这样,贡彩南和叶亦祖带着两个女儿一起回到了苏州。但是,北大荒仍然是他们魂牵梦萦的地方。他们享受着城市生活,却总是忍不住要与北大荒相比,共同的经历,让他们时时把北大荒当做参照,“我们经常说,忘本了,忘本了。”贡彩南说,“这就是缘分吧,这一辈子找到他,我心满意足了。”现在,八十岁的贡彩南经常会回忆起过去的事,想北大荒时的事,“自己想想,太开心了。”7.宋廷玉:孩子一出生,就被诊断为脑瘫,是煤气中毒造成的年2月份时,我们本来计划好采访白中原,中间临时决定赶去拍摄农场举办的冬季运动会耽搁下来,等回过头来再联系时,却听到白中原已经去世的消息,令人扼腕长叹,心中总是存着份遗憾。采访宋廷玉,就是希望能把这份遗憾补上。尽管白中原不在了,我们无法听他亲口讲述,但相濡以沫的妻子与他同甘共苦几十载,共同经历着那段艰苦的垦荒岁月。宋廷玉说,因为他在这里,就跟他来了走进宋廷玉家时,宋廷玉和她的大女儿、儿子很热情地迎接着我们。寒喧之间,偶然瞥见里屋炕上有人躺着,我们没敢贸然探问。宋廷玉,今年八十五岁,一个小巧精致的老太太,不太善讲,爱笑,看得出,年轻时就是个清秀漂亮的姑娘。她是河南南阳市人,退休时是八五二农场南横林子中学会计。她曾经也是军人,年1月入伍,在南阳军分区司令部军务科,只不过她在年就转业到地方,在南阳专区粮食局做财务工作。短暂的军人生涯,除了工作,她最大的成绩,就是收获了爱情。未婚夫白中原也在南阳军区司令部军务科工作。他们是自由恋爱,宋廷玉转业,并没有影响两个年轻人恋爱的热度,水到渠成地,两个相爱的人在年结婚了。结婚,本来意味着稳定的生活,相爱的人能长相厮守,但对于军人来说,这却是一种奢望。结婚不久,白中原也转业了,他没有留在南阳、留在妻子身边,而是去了北大荒,那个遥远而且寒冷的最北边。年轻时的宋廷玉宋廷玉因为有公职,暂时没有跟去,但她去探过一次亲。从城市走进荒原,无论是观感还是亲身体验,对比度都可想而知,吃的住的条件根本没法与城市比,但这就是他们未来将要安家的地方。对于宋廷玉来说,如何面对这样的生活,将是一场艰难的抉择。她是地主家庭出身,家里有点资产,从小的生活应该是很优越的,到了上学的时候就上学了,而且一直念到高中。年 爆发,部队征兵,还在南阳女中念书的宋廷玉报名参军了,被分到南阳军分区军务科,就在城市,坐办公室,抗美援朝时也没有去朝鲜,她就不应该是吃苦受罪的命。但是,宋廷玉探亲回去后,就办理了工作调转手续,从南阳调到北大荒。其实她也知道,只要她不肯来,丈夫早晚会调回去,但她根本就没这么想。宋廷玉说,“因为他在这里,所以就跟他来了。”到了北大荒,宋廷玉还是做财务工作,坐机关。白中原因为是军官转业,到北大荒之后,最初是在一分场当农业技术员,当时一分场的许多地号都是他划分的,后来就当干部,在总场工会、干部训练队等等。那时当干部绝不是好差事,且不说吃住与普通职工无二,干的还得比普通职工多,吃苦要在前面,有好事要往后退。他们的家虽然安在了总场,但白中原一直都是在下面的分场工作,连总场的干部训练队都是设在四分场的,他根本顾不了家,宋廷玉经常是一个人带着孩子过日子。年,宋廷玉怀二女儿的时候,不幸煤气中毒。那天晚上,白中原又没在家,家里只有宋廷玉带着刚刚五六岁的大女儿。宋廷玉被熏得昏迷过去,幸好大女儿还清醒,爬到门口打开了房门,才被邻居发现。宋廷玉被抢救过来了,不久,她生下二女儿,可孩子一出生,就被诊断为脑瘫,是煤气中毒造成的。后来,宋廷玉又生下了儿子。白中原仍然每天在下面忙碌。“文革”的时候,又被下放到四分场四队,放了一年多的马。宋廷玉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其中一个还是瘫痪在炕的,她还有工作,生活真的很难。无奈之下,夫妻俩把儿子送回老家,寄养在一个远亲家里了。宋廷玉对许多过去的事都说记不清了,说起上面这些事,也都断断续续。我们耐心倾听,细心询问,老太太要么只言片语,要么笑而不答,那笑容,竟透着些羞涩,让我们遥想她年轻时的秀媚和精致。岁月催人老去,北大荒的粗糙,硬是将一个纤柔女子,磨砺成心宽而迟滞的老人。或许她真的记不得曾经的过往,也或许她不愿意回顾遭遇的磨难,更或许早已看淡了世间诸事,那么说与不说,说得多说得少,在她,也就无所谓了。但是,上一代人的生命体验,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下一代,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暗示,或者说,凝成一份成长的基因。宋廷玉的儿子说:“把我寄养在别人家,不是自家,是别人家,是十里铺一个亲戚家的亲戚家,寄养在别人家。我是在别人家长大的。父母几乎没回去过,只记得回去过一次。小时候也不知道咋回事,大了也想,也想妈在哪儿?我七七年才回来,回来之后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子说得不多,只这几句话里,却有好几次重复着说“别人家”,可见从小被寄养的经历,在他的心里留下了多么深的印痕。这样的心理刻痕,别人感觉不到,也许他的父母亲也意识不到,但却会影响他的一生。宋廷玉的二女儿今年已经五十二岁了,因为脑瘫,不能动不会说,但却什么事都明白,看电视也都能看懂。我们恍然,躺在里间炕上的,就应该是二女儿。我们很想看看她,更想知道她的心理活动,但我们不能,甚至都不敢去打扰她,只是想一想,都觉得心酸心疼。她什么都明白,但她什么都不能说。又如白中原,本来应该能说出来的,只是因为突然离世,没有了机会或者没来得及说,就将所有的心里话连同他的一生经历都带走了。细想想,其实,白中原也好,宋廷玉也好,他们的经历,正是所有来到北大荒的复转官兵们的共同遭际,那是整整一代人的经历,如出一辙,大同小异。“大同”,是一个时代的风气;“小异”,则是个体的生命体验。而北大荒的女人,作为妻子、作为女人,无疑承载了更多的生命分量。垦荒,是男人的使命,同样是女人的命数。 (未完待续) 热点文章: 周总理之谜 胡耀邦:历史是混不过去的! 郎平:我属于球场,不属于官场 中国女科学家如中国女排一样,惊艳世界 胡锦涛同志生活足迹和精彩镜头 真相:庐山会议上最终整倒彭德怀的是一位政治小丑! 改革先锋项南的“被离职”演说 习远平:哥哥因受父亲的问题牵连,多次被关押审查。 邓小平看完军队接收香港方案,批了两个字:“软了。” 一位正国级领导的离任感言,发自肺腑,感人至深,值得所有笔杆子学习! 雷锋牺牲前为何没有被提干 大将之子亦清贫 有人说,如果抓”五人帮”,肯定有这个上将! 看看这位上将怎样送礼…… 董点军事儿:塔山有座将军陵园50年代,蒋介石曾经回过浙江? 中纪委八大“内鬼“先后被抓,反腐永远在路上! ▼把时间交给阅读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